明史十二讲-赵毅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0.4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第一讲 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
第二讲 “靖难之役”后的明朝政局
第三讲 七下西洋,扬天朝国威
第四讲 土木之败与明中期政局的转变
第五讲 差强人意的成弘治世
第六讲 明武宗与“豹房政治”
第七讲 “大礼议”与明代官僚队伍的大撕裂
第八讲 王阳明与“左派王学”
第九讲 怠堕贪婪的万历皇帝
第十讲 多灾多难的短命天子
第十一讲 事事关心的东林党议
第十二讲 有“道”无“福”的崇祯帝
第一讲 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是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一阙《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
元朝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还不到百年,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国祚是比较短的。这主要是由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后曾推行了一系列“汉法”,奠定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旧有的“草原本位”色彩并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在蒙语中仍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纪年方式汉、蒙并用,皇帝死后也同时有蒙、汉两种纪念性称号。如忽必烈按汉族传统的庙谥为“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国语”谥号则为“薛禅合罕”,意即贤明之汗。这表明元朝的皇帝实际上在一身兼任两种角色,既是汉族臣民的皇帝,同时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坚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存在隔阂,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历史学家钱穆评价说:“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赋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知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治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孟森先生也认为:“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当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爱民,亦有容纳士大夫一二见道之语,然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第一讲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其实,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元朝统治集团不能完全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都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元朝最后一个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后为北元昭宗)曾经说过:“李先生(按:指其师傅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晓。”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们同时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诚信徒,且因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都未能有太大作为。大多数蒙古、色目贵族对儒学的态度亦与皇帝近似。
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昔日作为治国主导方针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而与儒学格格不入的保守势力直到元亡都相当强大。顺帝一度讲习经史,但左右近臣多加阻挠。帝师则对太子习儒提出异议:“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不仅皇帝多不习汉文,蒙古大臣中习汉文者也很少。如元朝后期的右丞相阿鲁图就对顺帝称“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向左转,成为笑柄。
从成宗即位到顺帝在位中期,元朝的统治大体上一直维持着稳定。但在稳定的表象之下,社会又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地的武装反元起事绵延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武宗时,天灾人祸交织,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山东、河南地区蝗旱交作,疾疫流行,百姓父子夫妇相卖求食。顺帝在位初期,权相伯颜把持朝政。此时元朝地方政局不稳的状况日益严重。频繁的地方动乱更加深了以伯颜为首的蒙古保守贵族对汉人的仇视情绪。在伯颜主持下,元廷重申汉、南、高丽人不得持有兵器的禁令,凡有马者皆拘入官,禁汉、南人不得习学蒙古文字,又专门要求朝中汉官讨论对汉族起事者如何镇压。据称,伯颜甚至向顺帝提出了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
这段时间内,自然灾害也很严重。黄河发生决口,河南、北大片州郡罹水患,土地荒芜,人烟绝迹。河患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威胁漕运和濒海盐场生产,直接影响到元朝财政收入。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发民工十五万、戍卒二万人治河。工程持续数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大河南北的百姓经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元廷在此时大举征发民工,督责严刻,死者枕藉,怨苦之声载道。民工成批聚集于工地,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至正十一年(1351)治河工程开工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趁机策划起义。他们加紧宣传白莲教“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思想,并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治河工地上,同时散布谶语:“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河工挖出石人,递相传告,人心更加浮动。
这一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众于颍上,誓告天地,准备起事,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事未发而谋泄,被地方官捕杀。刘福通仓促起兵,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讲到:“起义的教徒都用红巾裹头,以区别于元朝的军队,当时人称之为红军、红巾或红巾军、香军;奉的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明教)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这两个神都是高鼻子,漥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了很稀奇,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指的是拜魔神,又叫作魔教。”
不过由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复杂性,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明朝》 ............
书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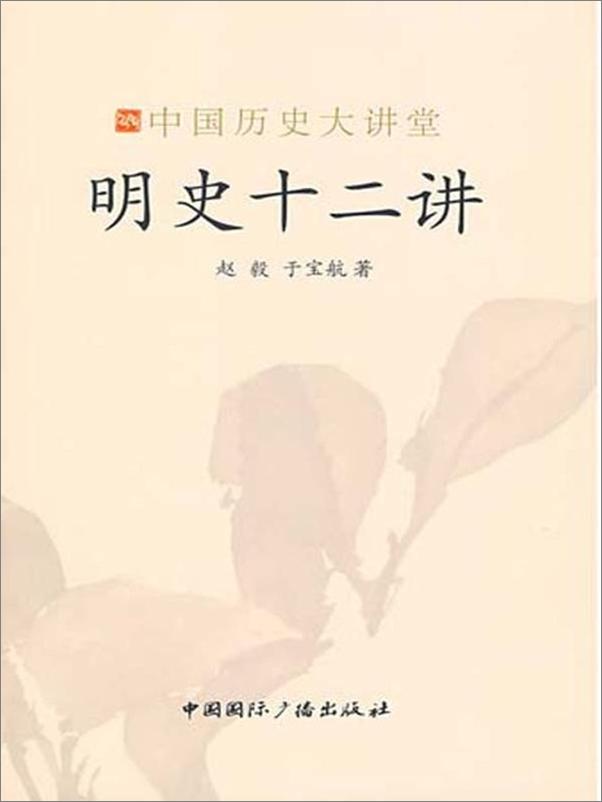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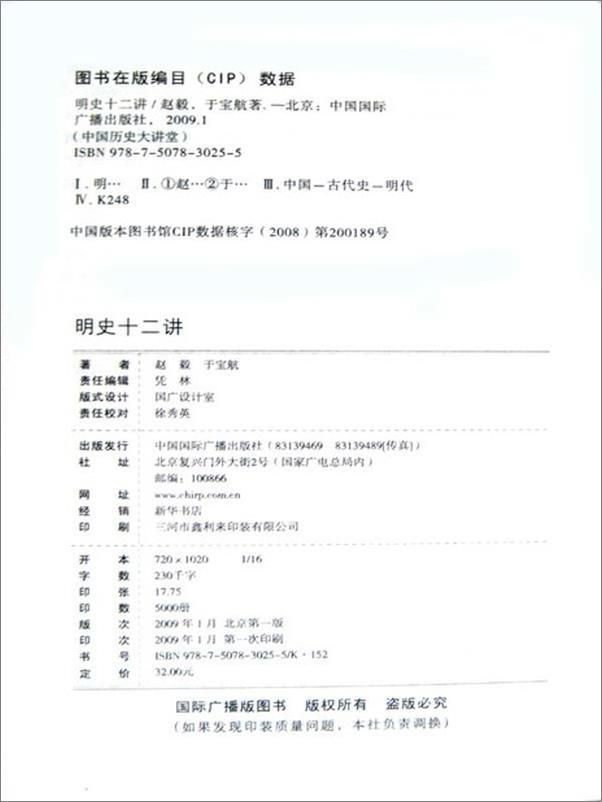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
书云 Open E-Library » 明史十二讲-赵毅 - (EPUB全文下载)
